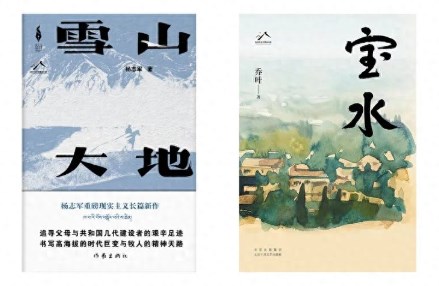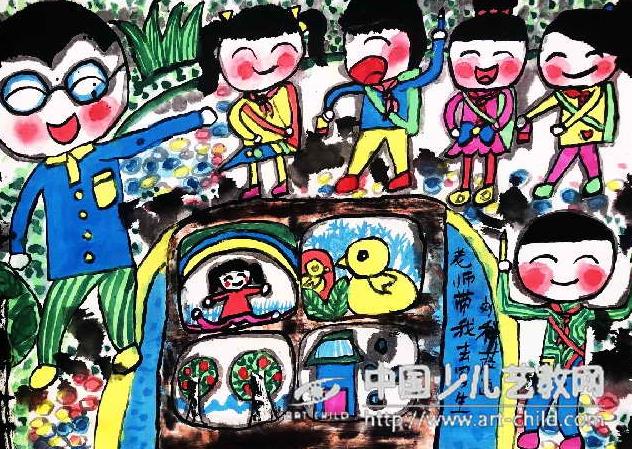郭进拴|闪光的足迹【三百三十二】
- 作者: 2855510
- 编辑:
- 来源: 会员中心
- 点击: 718
时间: 2025-07-17 09:07:18
郭进拴|闪光的足迹【三百三十二】
1980年夏天,张绍文先生为了给汝州剧院绘制巨幅《风穴图》,而专程到风穴寺体验生活,我也为了修改为《豫西文艺》写的《漫游风穴寺》而到风穴寺采访。我亲眼看到张绍文先生在方丈院挥毫泼墨,用了一天时间把方丈院四周的墙壁上挂满了他那力透纸背,铁钩银画的书法作品。他说:“为了搞好创作,要首先创造一种氛围。”农历六月十九午后,山风裹着暴雨,劈头盖脸地猛浇了下来,我和张绍文先生有意登上了寺西南侧的三层台阁钟楼来观雨。放眼望去,远山近水,烟雨蒙蒙,柏林危崖,时隐时现。整个古寺,云腾雾涌,似乎处于飘渺之中,令人有腾云驾雾之感。看着这浓墨泼洒的美妙图画,迎着满楼的清风,我们完全沉醉在了浓如醇酒的意境之中。他说:“这叫净寺雨,从我记事起,每年的六月十九古刹大会后都有这场雨。”
雾散天开,乌云惊退,天色更蓝,山水更美。一道彩虹,横跨山涧。张绍文老师领着文物保管所的所长吴元忠、我、还有他的爱人和小女儿,我们挽起裤腿,淌着溪水,从接圣桥下穿过,来到珍珠帘观瀑布。边走张老师边介绍道:“世间事都是有因有缘的,我爱风穴山白云寺也如此。我出生在书香家庭,大爷在清末读书很多,晚年教私塾,善书法好种花,家父从小随大爷就读,受其影响,也写一笔好字,以仁德处世,故受乡人尊敬。父亲的爱好又传给了我,所以我三、四岁对画、塑就有一种天生的偏爱,年稍长,随父到风穴寺赶会,一下就被那清静幽美的山林溪泉和巧夺天工的古建、塑像迷住了。此后每年都要去一次,特别是上小学期间,学校组织集体旅行,除了近郊的乌龙庙,就是风穴山。从入山到出山,每处景观、每座建筑、每尊塑像、每个匾额,都要细心地观察,如照像一样,深深地印在我心中。在校一篇文章背不好,而对风穴寺的情况却如数家珍,至今已半个世纪过去了,仍闭目即见,历历在目。几十年来我酷爱风穴寺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为什么?细想想:是她给了我知识,给了我智慧,给了我高级艺术享受,给了我无穷的力量;她更无形中启迪了我的人生,所以我无条件地爱她,像对待母亲那样忠贞、永远!也可能就是这个缘故,有机会就来看她,哪怕是到了她遍体疮痍,风烛残年,奄奄一息的时候,我的心还是那样地想着她,去到她的身旁,投入她的怀中,痛心、流泪、感伤、惋惜、长叹!因此才有1973年的专访,1978年的久住。静中不自觉地常想,我要尽最大努力无条件地协助国家和别人,来治疗她的疮伤,恢复她的青春,让她发挥她的天职:净化一代代人的心灵;孕育一代代的艺术人才;普渡众生,离苦得乐。也正是我对风穴寺的真挚之爱,虽不能终生相伴,幸而我身边有风穴山的‘九孔玩石’、‘艺术柏根’和‘石刻拓本’、‘昔日真影’。更使我欣慰的是,心中藏有风穴寺全部的原始照像底片。所以当我远离家乡,重病卧床的时刻,我的心又沉浸在风穴寺中,得到了无限的快慰。病好了,从死亡线上又活了过来。手虽不能画她那秀丽的容貌,只好用口述韵句,这一篇篇拙诗,就此出世。包括1978年在这里住时吟咏的草稿,终于用文字勾画了她昔日的风采,以备留给后人。因为近50年来风穴被破坏。虽已重修,但其面貌韵味,与昔时比有天渊之别。这些诗意比古人咏风穴的诗,要差十分之九。而古人的形容佳句也比真景相差十分之九,由此可知风穴原来的面貌。我只有真诚地记录她,可叹句子太拙笨,但这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张老师边说边吟了一首他即兴写的《雨后观瀑》:

山洪怒吼震苍岩,涧底秋花水半淹。
共话无声桥上坐,凉风浩气舞青衫。
他写的《重游风穴寺步李准诗韵》这样写道:
常来香积寺,最爱古林幽。
碧水环琪树,清风弄白头。
他注道:“1980年返古里见李准诗,步其韵偶成。1988年纽约‘四海诗社’选人《全球当代诗词选集》,后作隶书并李准行书刻石立于风穴寺大殿前。”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
上一篇:郭进拴|闪光的足迹【三百三十一】
下一篇:郭进拴|闪光的足迹【三百三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