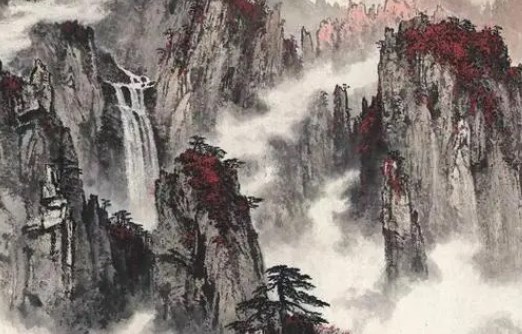许江:父亲的讲义
- 作者: 网络
- 编辑:
- 来源: 网络
- 点击: 224
时间: 2015-06-26 09:04:26
许江:
1955年生于福建福州,1982年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现中国美术学院)油画系,1988年赴西德汉堡美术学院自由艺术系研修,现居浙江杭 州,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许江长期担任上海双年展艺术委员会主任,并在高等艺术教育中推动了中国艺术教育的改革及推动新媒体艺术发 展。

一
我的父亲许永锡去世已经二十四年了,留在我身边的是他的一叠讲义,有半人高,这是其中的几本。纸已经碱化了,发黄发脆,不能翻,一翻就断掉了。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生命的分量》,我觉得这讲义像是铜砖,它的截面,只若岩层一般,有一种岁月沉积的感觉。
父亲的一生很坎坷,特别是“文革”,屡遭批斗,后来下放沙县。他曾是福州七中的语文老师,1960年代开始已经不能上讲台,当图书馆管理员,就 是那时开始像写书一样非常非常认真地写讲义。一个人做一件在那个时候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在为难以实现的事情做精心的准备。后来我每念及此都深深感动。 到“文革”时就有厚厚一叠,有一部分“文革”时被抄走了,有一部分被一位年轻老师拿走。后来到了沙县,我读中学,父亲务农。有一天,父亲在田里看到我和同 学骑自行车飞驰而过,后来,他和我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是能给我和我的同学上课,接着他做了个决定,给远在福州的青年老师写信,要求把讲义还给他。那个时候重 回讲堂讲课的希望其实更加渺茫,但是他觉得那是他的生命,他痛定思痛要把讲义追回来。
今天留在身边的父亲最重要的遗物,就是这叠讲义。其中包蕴着我父亲做事和为人的基本。我父亲一生做事情认真,小时候,父亲批改作文,我在他旁边 一盏油灯写毛笔字,其实不想写,写几下就看他干什么。我看他作文的批语,批语很美,仿佛在和学生交心,三两句能够把要害抓住,循循善诱,打开同学的心扉, 我当时觉得父亲的批语是很好的,书写的也很好看。不允许批语有涂改,错了怎么办,就用一个橡皮蘸一点点口水擦,错字就磨掉了。
父亲的讲义里,没有涂改,他写的是汉隶。他写词牌音调,平平仄仄, 编写注音字母,注音序,编页码。红蓝钢笔到红黑钢笔,两种颜色交替。那个时候纸很薄,笔一下就都透下去了。但父亲依然很认真把整套讲义装订好,完整地留存 着。“文革”中的生活似乎总在不停地填表,每次填表对我们这种家庭来说都是心灵的重压,偏偏碰上我父亲认真,每一次都要填得非常正确,我填完了给我父亲 看。我小时候练过刻钢板,刻钢板仿宋体字写得能够和印出来的一样,我父亲每次都让我用这种字体来写,每次填表就像大事一样,站在我的背后来监督。重压之下 总要写错,一写错就批评。最后就骂我,没少吵架。填表,批评,吵架,不欢而散。
父亲的认真通过填表吵架的方式给我深刻的影响,直至今日,我办事认真,举轻若重。每次学院填表,空格、字体,我都非常严厉。生活让我父亲用这种 方式来塑造我,年龄越大越认真,我想现在被我批评的人骂我,多少年后他们会感谢我。遇上要发言讲话,我尽量会花时间,有时晚上,有时是早晨,把要讲的话书 写成稿。这种书写的习惯,就是我的父亲传给我的,他塑造了我这个人,虽然他活着的时候我并不知道。当初只道寻常,今天却受益良深。
从这叠讲义身上,我还感到了“文心”。张载曾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这个“心”就是价值标准,核心价值。一般地说,这个文心就是情怀。父 亲的讲义把文人的情怀传递给我。我为什么喜欢象山,这个象山像极了我年少记忆里的一座山。我读的中学,那里也有一座山,像一个倒扣的米仓,于是有名“浮仓 山”。因为山脚一圈都是农民,我是在农民中间长大,但是我又不是农民,我在山上野,我很小就开始写诗。我父亲发现我有这个特点,同学有个聚会,让我拟一首 小诗,他再改一改,晚上让学生朗诵。我觉得这种文心,这种情怀在今天是至关重要的,实际上,中国美院在西湖边获得的就是湖山的情怀,进而是诗性的情怀。从 林风眠、潘天寿、吴大羽,到朱金楼、金冶,他们人生都充满了坎坷,是悲情人生,这种悲情没有让他们沉沦,这种坎坷锤炼着诗人的情怀,锻造着学院的根基,民 学的精神。
我把这样一种特征叫做“后文人艺术世界”,今天纯粹的文人没有了,但大学教授是新文人,他们的艺海生涯有几个特点,一是民学立场,源自民间,源 自底层。清代书画名家恽南田所说:“群必求同,求同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一个群体三五人,要有相同的地方,相和在哪里?在登览历史、念远怀人的地 方。黄宾虹先生,1948年回到南方,在上海小住几天,与上海友人讲演《君学与民学》,他说“发扬民学的东西,向世界伸出臂膀,准备着和任何来者握手”。 这段话放在今日都如此贴切,让我讶异。我们讲蔡元培先生从洪堡那里获得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也是民学的思想。
新文人的第二个特点是忧患意识,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他们立身于荒天古木,必要怀古。这是独特的登览,天下的登览。这种忧患意识相伴的 往往就是悲悯之怀。“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是一种悲怀;“只为浮云能蔽日,不见长安使人愁”,也是一种悲怀。实际上从林风眠、黄宾虹,到潘 天寿,都有这样的悲怀,并让这种悲怀深深地浸润和锤炼着他们自己。
第三个特点是群生活,这点非常重要,“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我们象山都是荒天古木,怀文心雅趣的人就会在这里形成群化的生活。我们讲 Academy,就是柏拉图的学院,三两人,沐着清风,穿着松袍,走过长廊,共同追赶真理。南怀瑾在二十多岁时,好朋友送他一首诗,“知君两件关心事,天 下苍生架上书”,知道他就关心两件事,一个是天下苍生,一个是架上著书。我从父亲讲义当中不断感受、不断激活的就是这种情怀,从这个根源上让我与学院历史 上的先师们的情怀接续在一起。
最后,我在我父亲这里还学到一种坚守,坚韧,坚持。他已经不能上讲台了,却坚持着把讲义写好,这是要传递一份家书。在农村最困苦的时候把讲义收回来,也是一种内心的坚守。这种坚持对于我始终都是一种激励。

二
这种认真态度、文心与坚守,从根本上塑造了我,无论是管理学校,还是对我的绘画都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绘画从最早的观念性作品,变为架上作品,从 最早的综合材料,回到纯绘画,从上海北京古城都市的天上俯看,变为葵园大地的远望。这样一个过程,我觉得整个的发展轨迹,越来越贴切地回到我自己。我现在 的立脚点是葵园。画葵就是画我们这代人,我对葵的感受很深,和“文革”有关系,我小时候生活的山上,也有葵,三两株。作为“文革”时共同的意象,我画的时 候始终想到我们这代人,始终有我自己的生命感受。
葵的经历中有一个很深的记忆就是我的哥哥。命运弄人,他的性格和我很不同,他少言寡语,以至说话有困难。我经常自责,我把两个人的话都讲掉了。 我们家所有倒霉的事都是他去承担。上山下乡时,我哥哥因为年龄太小,积劳成疾,吐血。回家时背了一个书包,从里边掏出两捆小松明,一种有很多油脂的松枝, 还有两个葵盘,因为捂在书包里已经有点烂了。我当时很伤心,我哥哥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吐血回来,带回来两个东西,一个汲取阳光的东西,一个点火的东西,但 是他自己的生命已经快要被时代耗尽。后来我们家就把他送到我外婆身边养病,外婆去世前一直交代:毛毛的一生你们要关心。
讲到葵,我们看到的可能不是青春向阳,而是命运怆桑,不是观赏性的亮丽,而是历史性的悲慨。我画的葵总有一份苦味,一种沧桑,一类老葵面对荒茫 大地时的命运轮替之感。我的葵都不是一枝葵,而是一片葵。因为我们一代人的命运本身就是相同的。我们这些人如此深刻地与那个时代结合在一起,趋于同化,所 谓“群葵”。这些东西都和我们的文心情怀有关系。所以我写很多诗,我会以诗化的方式讲话,以诗化的方式画画,我的画既不是写实的叙事性,也不是纯抽象的东 西,里头有这一代人生命诗化的东西。葵不是我们的象征,是我们生命本身。
我特别能够理解美院的上几辈。我特别能够理解林风眠在把自己的画作,一勺一勺地从马桶里冲掉时的心情——我特别想把那个马桶买回来,但据说是装 修时被扔掉了,我一直觉得,这个马桶是上个世纪中国文化命运的一个见证。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潘天寿1969年被拉到家乡去批斗,回来时在火车上用铅笔在香烟 壳纸上写的一生最后一首五绝:“莫嫌笼絷狭,心如天地宽。是非在罗织,自古有沉冤。”
诗的开篇写得很悲怆,但潘先生这代人的伟大之处,是不会滞留在悲怆中的,他迅速转换为对家乡的怀念“万峰最深处, 饮水有生涯。”后来我到过他家饮水有生涯的地方,很有感触。“千山复万山,山山峰峦好。一别四十年,相识人已老。”他讲的是他和家乡阔别40年,他不认为 他回去是被批斗的,而是回去回访家园,相识的人已老。潘先生乃神人也,在他去世40年后,2009年,杭州人民在他的墓碑旁边为他建了一个诗亭,两岸一百 多个诗人共同诵读他的诗篇。揭幕的时候,让我代表学校去发表一个讲话。我研究了一下,其去世后四十年就正好是2009年。这样一种文心让我读懂先辈的心 情,我自信只有我能够发现历史的密码,后来潘公凯先生问我,你怎么能看出这一点来。开幕现场所有的人都呆住了。
我深入到葵的世界,人的内心世界里头,咀嚼生命的沧桑和坚强,去把我的葵画起来。这几年画的葵园越来越硬气,越来越坚挺。为什么? 我觉得可能与我自身有关系。我的人在变,会投射到绘画里头。我一再的把葵在我心里诗化,来表达对生命的感受,应该说也是属于“后文人艺术世界”的感受。

三
前不久,高士明他们在香港汉雅轩的会议上做了个研讨会,讨论艺术的三个世界,一个是当代艺术世界,全球的平台;一个是社会主义文艺世界,曾经繁 荣过现在被宣告终结;一个是文人艺术世界,正奄奄一息。我认为没有绝然断分的三个世界,重要的是三个世界涵融三种情怀。当代艺术世界包含批判的情怀、实验 的情怀。社会主义文艺世界包含社会关怀的情怀。文人世界包含诗性的情怀。这些情怀互相交错。
我认为,今天的当代艺术世界是一个“后当代艺术界”。不是简单的“后”,在对多样传统追溯之时,内在是一种“破”,“文革”常说,不破不立,破 字当头,立在其中。批判意识,即是破和追问。这是后当代艺术世界的核心情怀,破与问的情怀。后当代艺术世界的弊端是全球化。今天的社会主义艺术世界也是一 个后社会主义艺术世界,是民与国族的情怀,民是想象的大多数,是国家利益联系着的共同体。这方面的弊端是体制化社会。后文人艺术世界是群与私的情怀。群是 荒天古木,私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品行。中国人重视的不是工具,而是肉身的体验。比方说烹调,西方人制造无数工具,中国人就一把刀,不同切法,中国人讲品 味,这个好鲜啊,“鲜”西语无法翻译。高级的品味诸如二十四诗品:雄浑,冲淡,典雅,高古……很难品,必要有高境才能体味。
这样一种品味可能带来的弊端是东方的自由化社会,这个后艺术世界在发生作用,形成新的格局,投射在某些艺术家就比较明显,就会划界。我觉得这种 讨论最有益之处,在于破解当代艺术世界和社会主义文艺世界二元对立的说法,这种说法是非常有害的,要么反政府的,要么是支持政府的,要么是反革命的,要么 是革命的,要么是西方,要么是中国的讨论。
我觉得这三个世界的讨论,可以用中国的文人情怀,从中国人自身的文化,来破解这个二元绝然的划分,从而建构一个多种资源、多个世界生生不息的格局。
四
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一个很好的口号。除了经济之外,很重要的就是文化复兴。有两个问题不能绕开,一个是全球和本土间的关系,一个是本土和今天艺 术世界之间的关系。这两个是我们今天绕不过去的。我觉得今天的中国美院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将传统的东西活化,让其中的正能量创造性地转化为当代的东 西。这是我们中国美院的优势。
这其中表现多样,范景中老师的理论思考,王澍的建筑探索,王冬龄的书法表演,邱志杰的艺术实验,高士明的策展观念,核心就是既具全球视野,又具本土关怀的传统活化的思想。
我觉得,在这里我父亲对我的教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我太清楚我父亲批评我是为什么,是因为太爱我,有诸多期望包蕴在里边,所以才批评。爱之 切,望之切。这让我在心里头,对具文心、有才华的人特别喜欢,而且我相信有才华的人会自我调节、自我复活,只要你给予他支持。比方说王澍,20年前我跟他 一起做关于观音谷公园策划的时候,发现他对传统很有体会,很有感受,所以后来他提出到同济学习,我马上推荐。他读了博士,第二年回来,我发现他读了很多 书,我说你回来,给你建一个建筑系。第三年,他的毕业论文叫《虚构城市》,找三个外面的评委写鉴定,我大概写了近五千字的评论,后来得了优秀论文,现在全 世界抢着出这本书。
王澍的建筑作品里,最重要的就是象山的建筑。他提出象山山北的建造思路,我当时觉得非常好,门窗走廊形成远望群山的观看的界面。建起来后,很多 人并不看好,后来山南还要建,我请刘家琨和同济、东南的朋友来评说这个建筑,也逼着自己画了《黑瓦与白瓦》。后来大家意见统一了。我又带着王澍去看将台山 下的皇宫遗址,那里有一个小坝,我说一定要设计这样一个坝,所有学生可以坐在坝上眺望青山。后来这成了象山山南的主脉,叫双龙戏水。在这个过程中,第一是 对这种文心和诗心的理解,彼此欣赏。第二用我们的方式来沟通,但不能教别人怎么做。我们学院非常好的地方在于自我激活、自我梳理、自我组织的方式。王澍先 是建筑系系主任,后来是院长,有了这样的平台,就好发挥。
范景中老师是我很钦佩的人。我进校时他还没有进校读研究生,后来听他的一个讲座,他说:“所有的知识都是一个漏网。打捞起有用的东西,漏掉更多 的东西。”后来他组织翻译贡布里希,成绩很大。尤其是2003年的时候我委托他写《中华竹韵》这一本书,结果他写了七年,其实写了四年的时候就可以出版 了,但是他一直改。这本书我读了受益良深。他研究了很多传统的东西,内涵宏博,最后的副题却很谦和,叫《中国古典传统中的相关品味》,这恰是一代文人的情 怀。
南山校园建好后,我只邀请一个艺术家做作品,让王冬龄先生写一堵大墙的字,他吃惊说要写这么大!正是这个任务,从此一发不可收,走遍世界。他感 谢我,因为是我逼出来的。我说这个学校只需要十个人,就是一个群,“群必求同,求同必相叫,相叫必于荒天古木”。我们学校就是一个群,南山、象山,风光天 然,恰如荒天古木,一定能够成就一番事业。有人说许江能够识人,能够容人,能够用人。该是谁的名份就是谁的。我觉得这其实是美院最主要的东西。我父亲对我 培养的方式,教会我从心里头崇敬人才,从心里头和他们相知,成就一番事业。
上一篇:梵高与阿尔小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