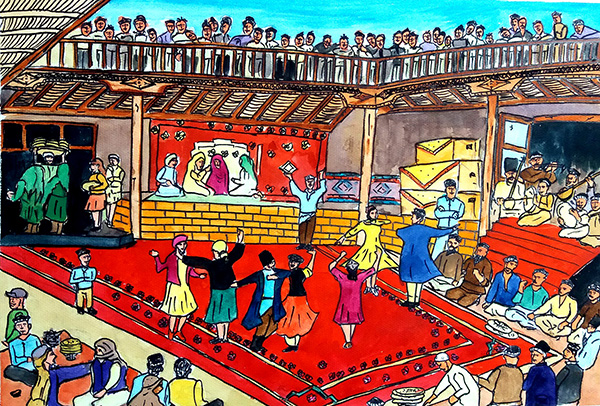戴上人工耳蜗 他就是最特别的摄影师
- 作者: 佚名
- 编辑: 董方婷
- 来源: 黑光网
- 点击: 2665
时间: 2022-02-17 08:56:58
你会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手也是一样的,我希望拍出那种静止的、雕塑的美。
克莱德曼的手和木心的手
8岁这年突然失聪,他说自己的听力是被外星人劫走了。直到18岁之前,他不知道自己将来该做什么。
琢磨这个问题的人远不止他本人。“耳朵也听不见,以后能干嘛呢?有一天妈妈的朋友说,‘要不给他开个小卖部算了。’妈妈如果听了那人的,我现在就是个小卖部老板了。”直到接触了摄影,他欣喜若狂,世界上终于有了适合自己做的事——相对于用耳朵聆听,摄影要求更多的是用眼睛看、用心去感受。
他去影楼做摄影助理,想学点东西。“两个月之后就不干了,因为拍出来的照片都一模一样,是流水线上批量复制的感觉。”后来又在一家儿童影楼当摄影师,只干了四个月。21岁,郑阳决定成为一名自由摄影师,在老家蚌埠租下场地开了间工作室,买些摄影器材。
2008年,他启动了《名流肖像》(以下简称“名流”)的拍摄计划。这一拍摄灵感来自出生于20世纪初的著名黑白影像摄影师尤瑟夫·卡什,他曾为上世纪众多杰出历史人物拍摄,留下堪称标志性的形象。
在摄影的黄金期,诸如《生活》这类杂志报刊的摄影记者在拍摄一名人物前通常有几天时间熟悉亲近拍摄对象,这在如今早已成为一种奢侈。一名普通的当代摄影师在抵达自己的拍摄对象前往往先要披荆斩棘闯过一片人际关系的丛林,而他所拥有的拍摄时间很可能不到一小时。
这样的环境更要求摄影师在最短时间里迅速捕捉到拍摄对象的特质,以他“名流”系列**个拍摄对象理查德·克莱德曼为例,郑阳当时是在钢琴家演出前排练时被允许短暂近距离接触他的。就是在那个稍纵即逝的瞬间里,他几乎是凭借自己的本能将构图中心设定在了对方的手部。
他的作品里还有一双著名的手,木心的手。这张黑白照片被放大到4米长,挂在位于乌镇西栅的木心美术馆。“当我看到照片被放那么大以后,更意识到手的象征性是非常重要的。站在它面前,我甚至会忘记这是自己的作品。谁拍的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一双诗人的手。”
他由此想到自己看过的那些古希腊雕塑,“很多雕塑在时间的长河里损毁了,只留下了局部,但那些局部都很美。你会想象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有什么样的故事。手也是一样的,我希望拍出那种静止的、雕塑的美,同时通过手部的美让人展开背后更多的想象。”哀愁是什么呢?知道就不哀愁了
那是在2009年,他拍摄木心。
2008年夏天,郑阳在家附近的一爿小书店里闲逛时看到了木心的书。当年10月,他决定前往乌镇寻找这名文学大家。“不知道他确切的地址,只看到书里写,是在东栅财神湾旁边。”他在附近转悠,问了几个看样子像是一辈子没离开过当地的老人,“木心的家在哪里?所有人都木然摇头,“我想,那个作家回来了,而他的邻居们都不知道。”
第二年,提前联系好,又去。从此每年总要到乌镇木心的家里与他同吃同住上两三天,老人去世前最后的影像几乎都是经他手留下的。
“他说,‘你拍摄一张照片,要像诗又不是诗,像哲学又不是哲学。’他给我看自己以前在欧洲拍的照片,‘最重要是构图和光线’。当时我带的耳机没有现在这么先进,交流起来有些困难。但他和人说话会认真看着对方的眼睛,因此让我感到自己被尊重。以我当时的阅历,并没有什么值得拿来和他对话的东西,所以我总是听他讲。”听说他曾有过这样一段经历后,每个人都会问他同样的问题,“吃得好吗?几菜几汤啊?”他很惊讶,“和这样的人在一起,你听他讲话都来不及,谁会在意吃啥……”
同一年,他做成另外一桩大事,跟随痛仰乐队踏上了他们成立十周年的巡回演出旅程。在那首著名的《公路之歌》里,主唱高虎反反复复念唱同一句歌词,“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一直往南方开……”当他和乐队成员一同坐上那辆七座的金杯面包车时,他想,歌词成为了现实。巡演路线从北京一路到云南,他和乐队呆了将近一个月。“有一段路程,车子的GPS突然失灵,但大家都很淡定。”后来回想起,郑阳觉得那像是人生的某种写照,知道自己是在对的路上,就不会为暂时的困窘着慌,也不需要别人来肯定。
生活的圈子被打开,天地突然变得宽阔。渐渐的他开始想,是不是可以来上海发展?然后就来了,他说“我做事情就是这样,做了再说。”
2012年左右,他在思南路香山路开了个小工作室,在那里度过了来上海后最初的时光。快乐或者不快乐的日子都有,他觉得也都正常。摄影师的收入不稳定,一旦赚了些钱,他都迫不及待拿来买摄影器材,因此日脚过得局促。26岁的他还很年轻,从蚌埠来到上海,满目所及皆是生疏。但社会现实,不会因为他年轻就特意眷顾。而他听力的缺陷,尤其成为对手们攻击他时**的武器。心意消沉时,他默默想起木心的话,“哀愁是什么呢,要知道哀愁是什么,就不哀愁了。”
“木心是一个不会说自己苦的人,这种精神力量对于刚出道的我帮助很大。这个世界有个这样的人,就像有个托底的东西,让你在面对困难的时候,想到这样一个人,就觉得可以过去。”在别人接纳前把自己推出去
他在上海主要从事商业拍摄,慢慢的收入变得更稳定。于是搬到龙吴路,租了个摄影棚,走上正轨。拍广告、写真,同时“名流”系列也在断续进行,如今拍摄人物已超过一百人。“简单来说,我是在用商业摄影养活自己的艺术创作。”
几年时间里,通过经纪公司和圈内人等的牵线,这一拍摄计划得以顺利进行。比如2013年两次拍摄了贝克汉姆,先是由一名记者带他来到这名中超代言人的活动现场、同年这名球星再次来到上海时,郑阳前往其下榻的瑞金宾馆再度参与了拍摄;拍摄尼古拉斯·凯奇,则是一家杂志在为他做专访时邀请郑阳担任摄影师的角色。
他感慨,自己接触过的大部分人很友善的,他们愿意接纳自己。但接纳的前提在于,他主动先把自己推出去,这即是他所说的:走出心门。在面对潜在的工作或合作机会时,郑阳通常的做法是先给对方看自己拍摄的照片,首先展示个人能力,让人家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但在这个圈子里建立起一些属于自己的名声前,他必须习惯于面对拒绝,有些拒绝并不善意。“有一次,对方认为我资历不够,拒绝了我的拍摄,而且认为我是故意模仿台湾口音。”这是郑阳没有想到的,虽然人工耳蜗帮助他较为顺畅地听说,但发音吐字毕竟和常人有区别,而这种区别竟被这样离奇地误解了。
“如果被拒绝,那是因为自己还不够格、不够强大,”他觉得自己既然选择走出家门,进入这个社会,就要准备好和其他人一样遭受社会的毒打。“这样的经历也让我反思,懂得人一定要提升自己,才会有和更多人对话的机会。不要玻璃心,因为不成功是正常,成功才是不正常。还是跌都不知道,怎么去预期人生呢?”游走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的人
摄影师们拍摄的对象多种多样,但无论人或风景,皆属于物质,而好的摄影师总是让人通过这层客观的实在感受到一些超越物质的精神。
这可以用郑阳拍摄歌手潘越云时的体悟稍作解释:
“她本人非常平易近人,可是面对镜头好像换了个人,像一个吉普赛女郎。我回来以后反复听她的《野百合也有春天》,眼前总是看到她面对我镜头时的那种眼神,这种眼神让我感觉特别美妙,难以解释的美妙,这就是摄影给我和自己的拍摄对象之间制造的一种奇特的化学反应。”
看着郑阳镜头下那些男女,我们意识到摄影师永远是游走在物质和精神中间地带的人,他们手中的相机成了实现这种游走的工具。这或许可以部分地解释他对于老相机的热情。他收藏的老相机中的一台是约1880年左右在巴黎生产的Pou lenc相机,核桃木机身,虽然型号未得到确认,但可知是18휓湿版相机。
这一时期,此后在法国如日中天的摄影师奥托·魏格纳刚刚在马德莱娜广场上开了自己的摄影工作室。谁知道呢,也许他当时就是用这台型号的相机为年轻的马塞尔·普鲁斯特留下了那些传世的影像。当郑阳凝视这些老相机和旧影像时,他很难不考虑传承的问题。在拍摄工作之余,他每年举办创作展览,进行多场公益讲座,他带着极大热情投入这些事情。他说,自己做的一切归根结底是为了让影像文化更深入人心,得到传承。后记
最后再分享一段郑阳最受震动的拍摄经历吧。
那是2014年,8 1岁的一代女神级影星夏梦在北京参加完影展后回到自己的故乡上海。在一个文化圈的朋友引荐下,郑阳在她住的酒店里完成了这次拍摄。她当时走路已经需要搀扶了,但还是给人留下尊贵的印象。暮年是人一生中最难堪的时光,他很少见到到老还体面的人。
然后,他透过自己的相机镜头惊讶地注意到,在夏梦所戴眼镜的有色镜片后面,她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但另一只眼中,竟然还闪烁着光芒。“不是每个人眼里都有光的。”他想,她这一生一定活得很干净,并且有一些始终深信的东西。
那次拍摄两年后,夏梦去世。郑阳至今仍会时常想起那次短暂的拍摄,并感慨原来人的尊贵全来自于自尊和自重。
(责任编辑:董方婷)
声明: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本文摘编仅作学习交流,非商业用途,所有文章都会注明来源,如有异议,请联系我们快速处理或删除,谢谢支持。
(原文章信息:标题:戴上人工耳蜗 他就是最特别的摄影师,作者:佚名,来源:黑光网,来源地址:http://www.heiguang.com/news/hydt/20220216/138142.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