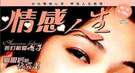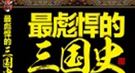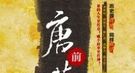再说历史小说《张居正》
- 作者: 本站编辑
- 编辑:
- 来源: 全息网
- 点击: 29
时间: 2012-06-06 17:57:53
本文摘自《文艺争鸣》杂志2004年第4期 作者:马振方
历史小说《张居正》从第一卷问世就多获好评,此后愈评愈高,所获奖项也日多日重。拙文《厚诬与粉饰不可取——说历史小说〈张居正〉》刊出之后,报上很快出现论争之文,或径与笔者商榷,或提高了赞赏《张居正》的调子。对于前者,已撰文作答;对于后者,拟于本文一并研讨。其实,前发拙文对该书的批评只谈了它悖逆历史的大部分内容,有的方面还没有涉及,对改革家形象的塑造状况更未深究,有的内容需要看到第四卷才好下笔。如今读罢全书,又读了诸家评赞,再说一次《张居正》,就教于论辩诸先生。
一、腐败是又一粉饰点
明史学者王春瑜先生认为,“张居正最大的弱点”是“在反对别人腐败的同时,自己却也在腐败”,“主要是行贿、受贿、滥用春药等”①。这看法有其道理,但“滥用春药”与行贿受贿不能同日语,可从“最大”中除去。所谓“行贿”,系指王先生在《明代宦官》和《中国反贪史》序言中说的以三万两黄金及大批珍宝贿赂冯保,而据《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所记,那是万历十年十二月直隶巡抚王国参劾冯保奏疏中的话,说“辅臣张居正病故,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张、夜明珠九颗、珍珠帘五副、金三万两、银十万两”,《天水冰山录》附录所记也当本此。既在张居正“病故”之后,不管有无其事,都不关乎他的“行贿”,所以这项腐败也应予否定。这样,张居正“最大弱点”的“腐败”就只有“受贿”一项。王先生说,《张居正》、特别是第四卷,对其腐败“有比较充分的描写”;笔者则认为,它并未得到切实的描写,反倒是作品对主人公的另一个重要粉饰点。
关于张居正的腐败,王先生多有研究和论述,除“在京买了大量房产”、“生活糜烂”之外,《中国反贪史》的如下文字甚得要领:
张居正在辽王被废之后,将其府第占为己有。先后任湖广巡抚的汪道昆、赵贤等用公款为之营建私第,张居正也欣然接受。《明史》说张居正“自夺情后,益偏恣。其所黜陟,多由爱憎。左右用事之人多通贿赂”。张居正被籍没时,折价约金银19.58万两,另有良田八万余顷。其家产虽不及大贪官严嵩,但也相当可观,其贪贿之状由此可见。
小说《张居正》对此写了多少呢?辽王宪火节被废为庶人在隆庆二年(1568),张居正“将其府第占为己有”或在隆庆六年以前,不在作品选写时段。但第三卷第十回回叙说:隆庆元年,“在众多地方官热心筹划帮衬下,加上儿子从北京也带了些银钱回来,几头一凑,张文明盘下了东门大街上的辽王府”。下文又说,隆庆二年辽王获罪被贬,“家产充公,包括荆州城中这一座朱梁画栋楼阁崔嵬的辽王府”,其后“物换星移人事代谢”,“辽王府变成了大学士府”。而到第十四回开篇大书特书的大学士府还是“位于东门大街”,“其前身是辽王府”,“张文明买下后重新修葺装饰”的。好像有两个由辽王府衍变而出的大学士府。前一个是张家在辽王被废前买的,后一个是人事代谢“变成”的,怎么变的,含糊其词。此种忽此忽彼、互相抵牾、语焉不详的文字显示了作者粉饰其事的矛盾心态。张居正死后被抄家,直接导火线就是他侵占辽王产业被张大其词地上奏朝廷,促使万历垂涎其财宝,从而改变了以往对已故首辅“姑贷不究”的态度。小说第四卷末只写下旨抄家,不提上述缘由,归根结底也还是为了避开张居正侵占辽王府事。
汪道昆(字南溟)与赵贤(字汝泉)等“用公款为其大建私第”,原有一个衍变过程。起初是为之建大学士牌坊,而其时张府“已有二坊,省此不为缺典”,被张居正谢绝。抚臣便将钱送到张家,“张家就用这笔钱翻修了辽王府,超支部分又由地方官一手给解决了。”②而在小说第三卷第十三回“揭家丑圣母识良臣”中,仍写为之建“大学士牌坊”,被张居正下令调人“拆毁”,使赵某难堪。其实,张居正为建坊、修府之事给楚抚汪、赵等写过多封谢绝信,调子大同小异,一面恳请他们不要动用公款和民工为他助修以“病民”、“市怨”,一面感谢他们的“雅情”、“盛爱”,从不严斥,更未处分,并大赞赵贤的政绩,甚至有“楚人思公不啻赤子之恋慈母”等语。结果是牌坊建了“六七座”之后,郧阳巡抚杨本庵还要为之“建坊表宅”。这类信看得多了,就会感到,它们既是谢绝新贿的表态,也是对旧贿的容纳和接受。明知“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还是接受了“去岁诸公所赐房价”,而且“已即给付工匠”。③连“六七座”牌坊都可容受的张居正怎么可能将刚刚建成的第一座牌坊就派人拆毁,使建坊官员大为难堪呢?拆牌坊描写是显而易见的粉饰之笔。至于用公款建私第,小说根本就没着笔。此回还写地方官曾将一千二百亩官地赠给张父,张居正大义灭亲,主动向皇上、太后禀报,自揭家丑,从而将他美化为清廉的“良臣”。这是“把他的弱点写成长处”的又一个典型例子。张居正受贿在京虽有(张四维、吴兑、殷正茂等多有“献遗”),更多则发生在江陵老家。对此,张居正大都心知肚明。万历四年,刘台参劾他的奏章,就历数其“夺”辽王“府地”,“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等贪贿之目,两年后他本人又回到江陵,亲所目睹。但他非但没揭露,还将“谈及其豪富”、与张父龃龉的御史李颐“外斥”。没有他在实质上的保护态度,其家的大量贪贿是不可能的。《张居正》把他写成“揭家丑”的“良臣”是不折不扣的粉饰和美化。
至于抄家所得,《明史》张居正传载“黄金万两,白金十余万两”,《反贪史》称“折价约金银19.85万两”,大约包括各种珍宝。而“良田八万余顷”不知据何文献,数量之大令人惊异。当时两广“所属官民田地山塘共三十二万九千六百顷”(《明神宗实录》卷一三一),张氏一家怎能有其四分之一那样多,太吓人了;正德之初,明朝各帝赐给诸王勋戚田地的总和才“八万顷”,张居正即便“私占废辽地亩”,也很难达到与此相等的大数目。王先生写的《中国历代贪官传·序》说张居正被抄家时“有良田八万余亩”,后来撰写的《张居正悲剧的启示》和《反贪史·序言》均易“亩”为“顷”,扩大百倍,与《反贪史》正文相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