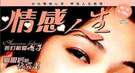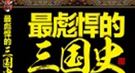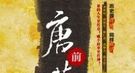马戛尔尼“谎言”:谁说乾隆皇帝不重视西方科技
- 作者: 本站编辑
- 编辑:
- 来源: 全息网
- 点击: 35
时间: 2013-03-19 16:43:04
核心提示:

本文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网站,作者:艾尔曼(BenjaminElman),原题:《马戛尔尼的“谎言”》
西方学术界有一种主流意见,即认为中国的科学只是十八世纪欧美的科学革命产物,中国不会出现资本主义、工业革命,而且没有科学的发展。事实上,中国科学与科技在十六世纪已有相当成绩,十八、十九世纪中国科学与科技发展的缓慢,不是因为中国人自身的封闭,而是由于当时作为中西交流的主要桥梁──十七、十八世纪的耶稣会士和十九世纪的基督教传教士,因为自身的宗教信仰与西方的科学有抵触,未能把当时欧洲的科学原原本本的输入,这导致中国人未能通过他们去了解当时欧洲的科学技术。
从傅兰雅(JohnFryer,1839-1928)及传教士对一八九五年中日甲午战争的反应可以看出,中国在这场战争中失败的同时,也证明了傅兰雅等传教士在中国传播西方科技以图改变中国的失败。然而,这些失败并不代表中国对科技没有兴趣。
中国科技的成长始于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清代艺术、仪器和技术的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非常重要,包括康熙时期的时钟制作、传统工厂的玻璃器皿和耶稣会士与圆明园建筑等在内的许多技术都与他们有关。此外,中国在明清时期所生产的瓷器也足以印证当时中国已经拥有先进的技术,尤其以景德镇瓷器最为突出。
问题是,为何中国在十八世纪没有经历欧洲的“牛顿世纪”(NewtonianCentury),而要等到中英鸦片战争之后,才认识到数理推论分析?
以往的耶稣会士曾靠着与欧洲一些科学院的联系,在科学发展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法国耶稣会士利用一七四二年出版的《SupplementtotheCompendiumofObservationalandComputationalAstronomy》一书(《历象考成后编》),向中国介绍牛顿(IsaacNewton),但该书也只是提到牛顿的名字,并没有系统地介绍他的学说。到了十八世纪后期,罗马教皇还没有废除关于中国礼仪的禁令,耶稣会士已经遭西欧的有识之士揶揄嘲笑。当时,法国人拉格朗日(Lagrange)、达朗贝尔(D’Alembert,)、孔多塞(Condorcet)和德朗布尔(Delambre)已经把数学及微积分中概率理论应用在实际生活中。例如微积分中的概率,提供了一个数理架构去评估个人意见的合理性,预测个人行为将会带来的后果。遗憾的是,耶稣会士在十八世纪从未把这些西欧的新科学传播到中国。
值得注意的是,仍然有很多论述以中国的外在因素作为理由,去解释为何牛顿式革命在亚洲那么晚才出现。有些人仍坚决认为清政府在一七九三年太过封闭,因此错失了认识刚刚崛起的现代世界的黄金机会,这些看法都不过是事后孔明。不论是马戛尔尼(GeorgeMacartney)、他船队的机械工匠,还是天文数学家登维德(JamesDinwiddie)在一七九三年到达中国的时候,都没有留意到,当时英国东印度公司在拍卖会中购得由德国制造的天象仪,上面已经涂有东方色彩的外表来迎合中国市场。后来,马戛尔尼参观了奢华的清帝花园,看到里面放满了“制作精良的工艺品如天体仪、太阳系仪、时钟和自动弹奏音乐的机械装置”,于是停下来思考他自己那些科学仪器的限制。当时有人提出,中国人应该会对英国的机器更感兴趣,但是因害怕聪明的中国人很快便能够复制那些出口的机器,结果有关建议就被完全搁置。
当英国人向乾隆介绍一艘名为“君皇”(RoyalSovereign)的军舰模型时,乾隆立即询问一些有关机械的问题,显示出他对舰上的大炮有着莫大的兴趣。事实上,马戛尔尼从来没有介绍过滑轮、气泵、化学和电动的装置,以及舰上的蒸汽机模型,马戛尔尼使团亦没有展示那个原本可能是作为礼物的经纬仪。经纬仪是当时测量经纬度的最新工具,相比满族沿用耶稣会士的测量方法去估计清朝的领土,经纬仪无疑更具效率。
这些仪器或交回英国印度公司,或是给了登维德。登维德向一些在广州的英国工厂介绍了这些仪器,并作了一些实验示范,当中亦有中国商人参与。对此马戛尔尼曾留下别具深意的记录:“如果登维德选择留在广州,继续他的示范,我敢说他很快便会发现,单是从中国学生那儿就能够赚取到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从一七九三年中国商人关注登维德的实验和仪器的情况来看,我们便会毫不诧异为何中国人在鸦片战争之后,能迅速注意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成果。
因此,马戛尔尼使团就得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结论。其实,早在1800年前,耶稣会士已经在中国替清朝监管着那些工业革命还未出现的传统工厂,并生产出许多奢华的工艺品。还有,中国早在十八世纪就已经拥有庞大的瓷器工业,生产和销售的瓷器数以百万计。令人感兴趣的地方是,与中国瓷器工业相似的英国伟吉伍德(Wedgwood)瓷器,到工业革命期间已经开始大量生产。可是清朝的瓷器工业由以往的传统经营的工厂过渡为现代工业,要等到十九世纪后期才能完成。如果说中国在十八世纪对西方学说已经相对地开放,那为何尚要等待?
在1800年间,中国已经拥有三亿五千万人口,已经能制造书籍、瓷器、精密仪器和手工艺品,为何我们总要抹煞当时中国在科技上拥有的技术和庞大的生产能力,而支持一个以欧洲为主导的观点,把现代科技的兴盛完全归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部分原因是那些从欧洲来的后继者,宣称他们十九世纪在亚洲贸易市场取得的成功,依靠的早期现代资本主义和科学。总之,早期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士,纵然面对大量工业生产及中、印贸易,他们视线所及的,仍然完全是另外一番光景。
(作者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及历史学教授。本文系作者在香港浸会大学创校五十周年(金禧校庆)期间,受邀在该校所做的演讲节录。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彭淑敏翻译。艾尔曼教授是美国汉学研究的著名学者,他的教学及研究范畴包括中国学术思想及文化史、中国科学史等。其最新著作《现代中国科学的文化史》上月刚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