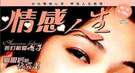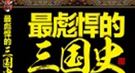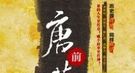《广陵散》作者嵇康:打铁出身的西晋音乐家
- 作者: 本站编辑
- 编辑:
- 来源: 全息网
- 点击: 85
时间: 2013-03-19 16:46:06
核心提示:
本文摘自《古代贤人的风采写照:魏晋名士的风流》 作者:司马放 出版社:崇文书局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风姿特秀。见者叹曰:“萧萧肃肃,爽朗清举。”或云:“肃肃如松下风,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为人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将崩。”——《世说新语?容止》
魏晋时期,《庄》、《老》盛行,士子们都以追求象征庄子理想人格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的仙子形象为美,所以名士们都非常注重仪容服饰上的修饰,出门前非但要傅粉施朱,熏衣修面,还要手执麈尾(羽扇),身配玉环、香囊等各种器物挂件,这样出门方能凌波微步,望若神仙。
可惜这些名士们往往“过犹不及”,只够得上“型男”的标准,却跟不上庄子“神男”的脚步。事实上,在如此追求庄子逍遥飘逸形象的魏晋南北朝,只有一个人在形象上真正直追庄子,那人便是嵇康。
嵇康身长七尺八寸(大约190公分,晋一尺为24.5厘米),粗头乱服,不加修饰,常常一个半月都不沐浴洗漱;可在当时人眼中,嵇康却仍然同春风般爽朗,同青松般俊秀,同美玉般皎洁,可见其真是天生丽质难自弃,美得让人无语了。一次,嵇康上山采药,一个老樵夫远远望见他的神采,不禁喃喃自语:“仙子啊,真是仙子啊!”
“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是当时人对嵇康的形象的一句定评,可以说嵇康的“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让后世所有仰慕庄子形象的士子均高山仰止,望尘莫及。
当然,与那些身娇体弱,上不了马,开不了弓,只能袖手谈玄的名士不同,身为皇亲国戚(娶沛穆王曹林之女长乐亭公主为妻)的嵇康还非常重视体力劳动。他常常与好朋友向秀在自家房舍外的大树下打铁,并通过打铁这样的实际劳动,自食其力,养活自己。魏晋风度中,嵇康打铁,陶渊明种地,都是士大夫主动走进社会,切身感受老百姓实际生活的表现,这在中国士大夫阶层中尤为难得。此外,嵇康还通过打铁挣钱,服务人民,练就了一身强壮的体魄。他那健美的肌肉,魁梧的身材,即便以古希腊的审美标准看,也是第一流的美男子。想那米开朗基罗的“大卫”比嵇康也只是形似,而远不及嵇康之神韵啊。
嵇康不但在形象上逍遥飘逸,在学问上也是一代宗师。相传,嵇康从未师从任何人,但却能从书本中自得其神。事实上,竹林七贤中,嵇康最为多才多艺,艺术成就也最大。论诗,虽然钟嵘的《诗品》中,将阮籍列为上品,将嵇康列为中品。但人们一谈起魏晋风度,首先想到的不是阮籍的“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阮籍《咏怀诗》),而是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饮酒之八》)和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入军》)。而相对于陶渊明的自然平淡,嵇康的“目送归鸿,手挥五弦”更是古今多少中国知识分子梦寐以求的画面啊!
论文章,嵇康更远胜其余六人,他的名作《养生论》、《答难养生论》、《琴赋》、《声无哀月论》、《释私论》等,皆清峻隽远,意蕴悠长。如《释私论》:“夫称君子者,心不措乎是非,而行不违乎道者也。何以言之?夫气静神虚者,心不存于矜尚;体亮心达者,情不系于所欲。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情不系于所欲,故能审贵贱而通物情。”全文流畅自然,简洁明晰,行云流水间,其“越名教而任自然”之论点宛若清水出芙蓉。事实上,纵观中国文学史,这样简洁流畅,意脉连贯的论文也是不多见的。
论音律,阮籍最好的琴曲《酒狂》也远不能同嵇康的《广陵散》相媲美。除《广陵散》外嵇康还创作了被称为“嵇氏四弄”的《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琴曲,并与蔡邕的“蔡氏五弄”合称“九弄”,是中国古代一组著名的琴曲。隋朝时炀帝甚至把“九弄”列为朝廷取士的条件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大。至于《广陵散》,又名《聂政刺韩王》,是嵇康根据古曲加工而成,与俞伯牙的《高山流水》并称为“稀世之音”,为中国五千年音乐史之最高成就。
#p#副标题#e#论书法,嵇康更以一手草书独步当世,凭他那洒脱的个性,自然的玄性,以及诗赋音律全方位的艺术功底,嵇康的草书既酣畅淋漓,又有龙凤之美,难怪唐朝张怀瓘要在他的名著《书断》中对嵇康的不在笔墨、出自自然的书法风格赞叹不已。
当然嵇康最令人高山仰止的既不是他的天姿秀出,也不是他的才情四溢,而是其独立健全、震古烁今的人格伟力。嵇康所处的年代正值魏晋之交,当时司马氏为稳固统治,以名教的名义大肆杀戮异己,诛灭了曹爽、何晏、夏侯玄等八大名族。《晋书》也屡次提到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可见政治环境之险恶。嵇康的一个至交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为司马昭心腹并身居吏部侍郎这样的高位。一次他离职高升,便邀请好友嵇康来接替自己的位置。想必山涛这么做也出于好心,他希望嵇康能借这次机会改变与司马氏不合作的态度,以便躲过血淋淋的屠刀。可他太不了解自己的朋友了,或者说他太低估人类的高贵品质了,刚肠疾恶的嵇康接到邀请后,为显示决不于司马氏合作的态度,断然作书与举荐他的山涛绝交。
在这篇响震千秋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先是将山涛这类趋炎附势的官僚描写成“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的没主见的怪物;紧接着又阐述自己追逐自由的决心,就如麋鹿虽身挂金饰,但仍志在丰草;然后,嵇康又写了自己不适合做官的“必不堪者七”和“甚不可者二”,将矛头直指权臣司马昭,公开宣扬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要知道,当时名士王肃、皇甫谧等人为替司马氏篡位制造礼教依据,杜撰了许多汤武周孔的名言。嵇康在这里说自己“非汤武而薄周孔”,等于公开反对司马氏篡魏,这无疑戳到了人家的疼处,据说司马昭读毕此文,对嵇康深为嫉恨,杀心顿起。
嵇康作书与举荐他的挚友山涛绝交,体现了他不为强权所迫,不为荣华所惑的独立人格。然而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统治者都是外仁义而内阴狠的,他们绝不会容忍任何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出现,去揭露他们的虚伪,去挑战他们的专制,更何况嵇康面对的是以滥杀滥赏闻名的司马氏集团。所以,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一出,他的生命也就进入了倒计时。
孟子曾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这句话也被后人视为一个儒者所应有的气节风骨。可是,那个年代,司马氏集团虽然口口声声说“以孝治天下”,但路人皆知,司马氏集团最是不忠不孝。公元260年,司马昭甚至指示手下刺杀皇帝曹髦,而面对弑君这样的大悖伦常,朝野上下却一片鸦雀无声。那些平日里满嘴之乎者也的儒者,全都瞎了吗?不,是他们在荣华前丢弃了“富贵不能淫”;那些平时一口一个孔曰成仁、孟曰取义的儒者,全都哑巴了吗?不,是他们在刺刀下忘却了“威武不能屈”。那个时候,只有嵇康,也唯有嵇康,敢直言揭露司马氏的虚伪丑陋,敢辛辣批判司马氏肆意歪曲的“汤武周孔”。可见,被后世诸多假道学批评为“离经叛道”的嵇康,才是儒学最坚定的捍卫者和执行者,他捍卫了儒学最原汁原味的精神内核,决不允许半点政客的虚假污秽去亵渎它。
赏心悦目啊,嵇康非但“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直追庄子的“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他的“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颜延之《五君咏?嵇中散》)同样直逼孟子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在嵇康身上真正体现了道学“神人”和儒学“圣人”的统一。
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墨迹未干,短短数年之后,前蜀的臣子李密同样面对司马氏集团的征召,“聪明”的他挥笔写就了一篇《陈情表》,从而成了如今中学教科书的必备篇目。
李密的《陈情表》虽然同样是表达自己不愿出仕的意愿,但与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的酣畅淋漓、锋芒毕露迥异的是,这一中学教科书名篇,言词委婉,意蕴曲折。李密紧抓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的大纲,诚惶诚恐地假借祖母年老体弱需人尽孝为由,既卑微又讨巧地谢绝了晋武帝司马炎的征召。
如果说司马氏集团“以孝治天下”是虚伪的、无耻的,是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掩他们的残暴,那么,身为亡臣,对蜀汉有眷恋之情,对亡蜀的司马氏集团有怨恨之意的李密,以老祖母为挡箭牌,从而拒绝征召,又何尝不是同样的虚伪无耻?又何尝不是同样用“孝道”的外衣来遮挡自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大丈夫人格的沦丧呢?
从这点上说,李密甚至不如明清之交的吴伟业。人家吴伟业虽也是大丈夫人格沦丧,但好歹没拿“九十六岁的老祖母”说事儿,反而在自己的临终绝笔中写得明明白白:“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人世事,几完缺?”(吴伟业《贺新郎?病中有感》)明言自己是贪生怕死,苟且偷生,既难以面对牺牲的故友,也知道难以避免后世的耻笑。吴伟业虽说的是糗事,但一字一句,饱含血泪,情感真挚,让人多少生些怜悯之情。哪像李密的《陈情表》,什么“臣亡国贱俘,至微至陋”,什么“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谨拜表以闻”,也太假了吧(尽管站在他的立场上,他也是没办法)。
#p#副标题#e#当然,笔者在此并不是要否认李密《陈情表》的价值,毕竟存在即价值,《陈情表》那么多年都是中学教科书的必选篇目,自然是有它的价值。毕竟,对现实生活中的你我而言,平时向领导上级请个假,写份报告什么的,李密的那种意思隐晦,语言婉转的“陈情法”,还是有很高实用价值的。毕竟,现实生活中,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那样放言无羁,锋芒毕露。若真是那样,那倒是有损和谐社会的和谐了。
嵇中散①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②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太学生三千人上书,请以为师,不许。文王亦寻悔焉。——《世说新语?雅量》
正如前文所说,表面以孝治天下,但实际上滥杀滥赏的司马氏集团,对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中所流露出的决不与他们合作的态度,和公开反对他们篡位的立场,都深为忌恨,必杀之而后快。
果然,就在《与山巨源绝交书》发表的一年后,司马氏集团便拿嵇康的另一封私人信件说事儿,诬告他“言论放荡,害时乱教”,并以此为由,判处他极刑。
这件事的经过是,嵇康的一个朋友吕安,其妻子被他的哥哥吕巽奸污,当吕安得知此事后,准备告发吕巽。不想,吕巽竟恶人先告状,诬告吕安不孝。早已投靠司马氏集团的吕巽控告与嵇康同属一个阵营誓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吕安。司马氏集团当然党同伐异,判吕安有罪,并将他发配边疆。面对朋友的无辜蒙冤,早知此事原委的嵇康,自然义愤填膺,断然写下《与吕长悌绝交书》,信中为吕安仗义执言,怒斥吕巽(字长悌)的禽兽行为。
自古以来,将他人文章或书信中的只言片语,单独剥离出来,断章取义,并以此为由,影射出罪名,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铲除异己的惯用手段。而嵇康的这封情绪激烈、意气慷慨的书信,自然也撞到了司马氏集团的枪口上。很快,这封信就被吕巽告发,司马氏集团也正好以此信为由将嵇康逮捕下狱。
负责审理此案的是司马昭的心腹宠臣,时任司隶校尉的钟会。出身高等士族的钟会(魏太傅钟繇之子)虽只比嵇康小两岁,但早年却是嵇康的疯狂粉丝。一次,钟会写了篇《四本论》,很想让嵇康指导一番,借名家点评,增加自己的学术声望。可是,刚走到偶像家门口,钟会担心一旦嵇康就自己的《四本论》发问,而自己又难以应对,那岂不是糗大了。所以,亦步亦趋的钟会,终于还是没敢敲门而入,只是偷偷地将《四本论》从嵇康家的窗户下塞入,然后就三步并作两步地跑掉了。
后来,钟会渐渐得宠于司马昭,成了朝廷里的红人。事业有成的钟会,便决定再次拜访嵇康。这次为了显示对嵇康的尊重,钟会特意穿上了精致华丽的衣裳,并带了大量宾客,一同步行去洛阳城外拜谒嵇康。
钟会一行人浩浩荡荡来到时,嵇康正与向秀在柳树下打铁。嵇康似乎并不喜欢这一大群贵族子弟来打扰他的安宁生活,所以并未招呼他们,而是继续埋头打铁。钟会几次都向他投去渴望交谈的目光,但嵇康看都没看他一眼。就这样,钟会和他的一大群宾客在柳树下默默地许久注视着嵇康打铁。最后,见嵇康始终没有接待的意思,钟会也只有无奈地招呼他带来的宾客,一同打道回府。临走时,嵇康忽然放下锤子问道:“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会听后,也答道:“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一问一答,看似都漫不经心,却反应了二人的博学和才智。因为,答句和问句显然都语出佛学经典《维摩经》第五卷,说的是文殊菩萨探病维摩诘的故事。维摩诘的话是:“善来文殊师利!不来相而来,不见相而见。”文殊菩萨的回答是:“如是居士,若来已更不来,若去已更不去。所以者何?来者无所从来,去者无所至,所可见者更不可见。”也就是说,嵇康问“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是在表达对钟会的欢迎,但也提醒他,朋友相交,贵在知心,不必如此刻意。而钟会虽也引用了文殊菩萨的答语,为自己争回了些颜面,但显然他的胸襟远不及文殊菩萨那般开阔、豁达。从此之后,钟会就对嵇康由爱生恨,一直想找机会报复。
这次钟会以司隶校尉的身份主审嵇康案件,自然要好好利用,对嵇康加以报复。他先是进言主子司马昭,说道:“嵇康,是当代卧龙,千万不能让他有机会施展才能。今日,主公治理天下,已高枕无忧。唯独需要提防嵇康这样不肯合作的大名士啊。”话中,将嵇康比作司马氏的死敌卧龙——诸葛亮,无疑刺激到了司马昭最脆弱、敏感的神经,可谓阴毒至极。
竹林七贤之首的嵇康被无辜下狱,在魏国上下激起了轩然大波。一时间,数千名在地方上极有声望的豪杰之士,纷纷上书,要求同嵇康一同入狱,并希望以此向当局施加压力,营救嵇康。面对如雪片般飞来的封封请愿信,司马昭显然感到了嵇康强大的政治号召力,正处于杀戮政敌前的紧张和亢奋状态。
#p#副标题#e#此时,候准时机的钟会,又乘机火上浇油,他向司马昭说道:“今日四海升平,天下归心,但嵇康却始终不愿臣服主公,而且怠慢礼法,藐视朝纲。昔日,姜子牙诛杀齐人华士,杀戮鲁人少正卯,都是因为这些所谓名士,恃才傲物,蛊惑群众,轻蔑礼法;所以圣人才执礼教之剑,杀之。现在,嵇康、吕安等人言论放荡,煽动民众,诽谤礼教,为自古圣贤所不能容。所以,主公您应当处死嵇康,以敦正风俗,清洁王道。”这一番话,博学巧思的钟会,特意用姜子牙和孔子诛杀不愿与之合作的名士的典故,对司马昭杀害嵇康,加以鼓动。而早对嵇康有必杀之心的司马昭,听到圣人也有过杀害异己的例子,更是血脉贲张,理直气壮。当下,就签署了嵇康的死刑令。(孔子诛杀鲁国名士少正卯一事,最早见于《荀子?宥坐》篇,但其真实性历来存在很大争议。这里钟会引用此典,很可能是以讹传讹。)
一代大名士嵇康,就这样因为一封与朋友绝交的私人信件《与吕长悌绝交书》,而被统治者扣以“言论放荡,害时乱教”的罪名,判处死刑。这样的判罚看起来强词夺理,不可理喻,但绝非司马氏集团所独创,也非司马氏集团所独有。事实上,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在对待不肯与之合作的具有独立人格的大名士时,都不屑于精选案件,巧设罪名,而都喜欢随手拈来一个案件,胡乱地扣上一个罪名,便草率结案,置之于死地。这种做法看起来荒诞不经,但却有其深刻的用意。因为唯有这种毫不讲理、专横野蛮的杀戮,才能彻底显示专制的绝对性,造成对人心巨大的威慑,营造社会空前的恐怖。所以,这样简单荒谬的冤案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数不胜数。而这样的恐怖政治手段,也没什么技术含量,归结起来,就十二个字:胡乱逮捕,草率结案,迅速处决。
为了尽量降低政治风险,嵇康被判死罪后的不久,就被推上了法场。一早就得到风声的魏国上下各界,迅速行动起来。黎明时分,三千名太学生集体上书司马昭,要求拜嵇康为师,以期免其死罪。与此同时,魏国地方上的数千名豪杰,也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声援嵇康。而嵇康在朝中的挚友阮籍、山涛也曾先后面见司马昭,希望能救嵇康一命。
太学生的集体上书,地方豪杰的群起响应,当时名士的联名救援,无疑在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示威。然而,中国历代的专制统治者,从来也没有在民意前,退让过哪怕半步。客观地说,嵇康的强大政治号召力,反而加速了他的死亡。
司马昭先是不动声色,支走了阮籍、刘伶等人,后又密令大量军队戒严在刑场四周,准备随时应对可能发生的“突发事件”。等一切部署妥当,他才派人进入法场,向大家宣布他维持嵇康死刑原判的法令。
此法令一经宣读,在法场上炸开了锅。三千血气方刚的太学生群情激愤,他们开始推搡戒严在刑场四周的卫兵,小规模的肢体冲突也在刑场四周,时时暴发,随处可见。“释放嵇康,释放嵇康”的声浪更是一浪高过一浪,响彻刑场所在的东门。此时,面对戒严的士兵,激愤的学生,喧闹的刑场,还有身边的亲友,嵇康的眼神却还是空无一人的孤独。他回头看了看日影,知道时候尚早,就对哥哥嵇喜说:“哥,我的片玉古琴带来了吗?”
“我带着,喏。”嵇喜哽咽着把琴递给了嵇康。
嵇康摸着他心爱的片玉古琴,若有所思,随后便用他那纤尘不染的双手,拨动了银色的琴弦。
只听,嵇康的琴声一起,喧闹的刑场立刻平静了下来。那琴声起先是如此的空灵、飘逸,令人仿佛置身于秀美的峨眉之巅,望着烟雾缭绕的层层白云,感受着自然的伟大和神奇。然后,这琴声,又变得慷慨、激越,让人好似置身于血染的战场之上,望着仁人志士的前仆后继,感受到生命的顽强和不屈。一会儿,这琴声,又变得清秀、温婉,让人似乎置身于清丽的小桥之边,望着生生不息的股股清泉,感觉到自然的永恒和圆满。嵇康的亲友,三千多太学生们,静静地聆听着嵇康最后的琴曲,听着听着,在场的所有人包括部分戒严的士兵和监斩的官员,都忍不住泪如雨下,泣不成声。可是,此时嵇康的眼神,依旧是那样空无一人的孤独。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嵇康《赠兄秀才入军》),嵇康临刑弹琴时,心境还是那样的超越、平和。
随着嵇康在片玉古琴上的最后一次弹拨,他完成了中国文化中永远值得后人高山仰止的一段画面。
“袁淮曾让我教授他《广陵散》,可我没答应,如今这《广陵散》从此成了绝响。”嵇康在完成中国文化里“永恒的瞬间”之后,略显遗憾地说。
“斩。”大约三分钟后,随着监斩官的一声令下,一颗集道家“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与儒家“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人头与身体分离了。嵇康,时年仅三十九岁。
“上帝死了”。对当时尚有良知的士子百姓而言,嵇康的被杀,无异于“上帝死了”。此后,在司马氏集团的淫威前,他们纷纷选择了逆来顺受,再没有人敢像嵇康那样站出来,直言揭露司马氏集团虚假丑陋,恐怖凶残。就连“竹林七贤”的其余六人,也统统归顺司马氏帐下,不敢再有箕山之志(嵇康挚友向秀在嵇康死后,也乖乖去司马氏手下任职,在司马昭面前,申明自己没有“箕山之志”)。
当然,就如中国音乐史上的伟大作品《广陵散》通过《神奇秘谱》得以流传至今一样,嵇康的高大独立的人格,虽然可能被扼杀一时,但总有伸张的一天。正如南朝著名诗人颜延之在《五君咏?嵇中散》中所言: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先,吐论知凝神。立欲忤流议,寻山洽隐论。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
诗末,“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慷慨悲壮,响彻古今,历来为嵇康的仰慕者所激赏。其中,“龙性难训”一词,后来更是演化为对那些具有高尚人格,又敢于坚持自我,并为之不懈奋斗的人们的赞誉(这点上说,褒义的“龙性难训”迥异于贬义的“桀骜不驯”)。
对于今天生活在和谐社会的我们而言,或许我们没必要像嵇康那样,认真到勇敢,追求生命的绝对高尚与纯洁。但我们同样可以像嵇康那样追求自我生命价值的高度自觉。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高度尊重自己的人生观、审美观,坚持自己的理想和对自我人生价值的追逐,尊重并创造出“自我”的独一无二。
总之,虽然我们做不到与其苟延残喘,不如烈火涅槃,但对“自我生命”的高度认同,我们还是力所能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