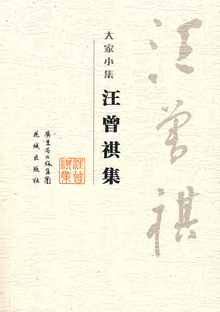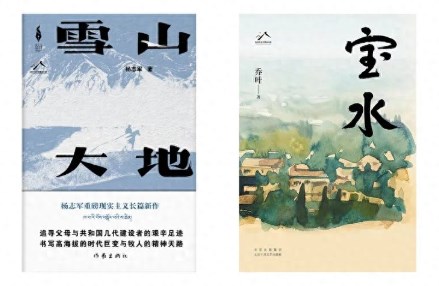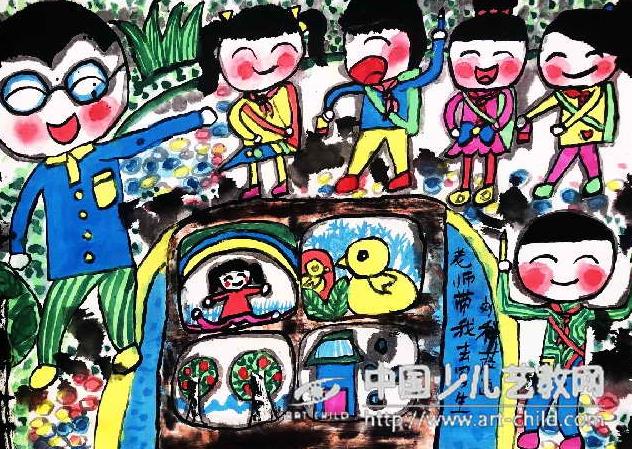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零三】
- 作者: 2855510
- 编辑:
- 来源: 会员中心
- 点击: 656
时间: 2025-04-23 08:55:19
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零三】
“现代以来,我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交流就一直在进行,白话文、现代小说、现代诗歌等都是借鉴国外又进行民族创造的成果,其中一直存在着学习和坚守自身传统之间的关系的命题。如何在博采众长的同时,打造具有中国气象、中国精神的文学传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希望《汪曾祺集》以及更多当代作家原创作品的出版,能为这个问题的探索与解决贡献一点绵力。”陈杰说。汪曾祺,1920年3月5日生于江苏省高邮市,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汪曾祺在短篇小说创作上颇有成就,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
1935年秋,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入江阴县南菁中学读高中。1939年夏,汪曾祺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愿考入西南联大中国文学系。1950年,任北京市文联主办的《北京文艺》编辑。1961年冬,用毛笔写出了《羊舍一夕》。1963年,发表的《羊舍的夜晚》正式出版。1981年1月,《异秉》在《雨花》发表。1996年12月,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推选为顾问。
1997年5月16日上午10点30分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77岁。汪曾祺的散文没有结构的苦心经营,也不追求题旨的玄奥深奇,平淡质朴,娓娓道来,如话家常。
他以个人化的细小琐屑的题材,使"日常生活审美化",纠偏了那种集体的"宏大叙事";以平实委婉而又有弹性的语言,反拨了笼罩一切的"毛话语"的僵硬;以平淡、含蓄节制的叙述,暴露了滥情的、夸饰的文风之矫情,让人重温曾经消逝的古典主义的名士风散文的魅力,从而折射出中国当代散文的空洞、浮夸、虚假、病态,让真与美、让日常生活、让恬淡与雍容回归散文,让散文走出"千人一面,千部一腔",功不可没。
汪曾祺的散文不注重观念的灌输,但发人深思。如《吃食和文学》的《苦瓜是瓜吗》,其中谈到苦瓜的历史,人对苦瓜的喜恶,北京人由不接受苦瓜到接受,最后谈到文学创作问题:"不要对自己没有看惯的作品轻易地否定、排斥""一个作品算是现实主义的也可以,算是现代主义的也可以,只要它真是一个作品。作品就是作品。正如苦瓜,说它是瓜也行,说它是葫芦也行,只要它是可吃的。"汪曾祺的小说充溢着"中国味儿"。正因为他对传统文化的挚爱,因而在创作上追求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中去。在语言上则强调着力运用中国味儿的语言。汪曾祺小说中流溢出的美质,首先在于对民族心灵和性灵的发现,以近乎虔敬的态度来抒写民族的传统美德。为此,他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受戒》和《大淖记事》。作家汪曾祺曾这样评价自己:“我觉得我还是个挺可爱的人,因为我比较真诚。”而熟悉汪曾祺的许多朋友谈论他时,最想说的一句话并不是“先生是一个小说大师”,而是“先生真是一个可爱的好老头儿”。
汪曾祺一生经历了无数苦难和挫折,受过各种不公正待遇,尽管如此,他
 汪曾祺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贾平凹评)
汪曾祺始终保持平静旷达的心态,并且创造了积极乐观诗意的文学人生。贾平凹在一首诗中这样评价汪曾祺:"是一文狐,修炼成老精。"[2](贾平凹评)
汪曾祺博学多识,情趣广泛,爱好书画,乐谈医道,对戏剧与民间文艺也有深入钻研。他一生所经历的轰轰烈烈的大事可谓多矣,例如启蒙救亡、夺取政权、反右斗争、"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但他深感现代社会生活的喧嚣和紧张,使读者形成了向往宁静、闲适、恬淡的心理定势,追求心灵的愉悦、净化和升华。[3](中国作家网评) 有一年,《工人日报》请汪曾祺给一个工人作家班讲课,题目是“小小说的创作”,但汪曾祺在课堂上却大讲文学与绘画的关系,还带来了自己的一幅花鸟国画,有个男同学问:“能不能送给我?”汪曾祺说:“处对象了吗?”男同学说有了,汪曾祺就爽快地回答:“那好,就拿走吧,送给女朋友,这叫——折得花枝待美人!”
广东作家陈国凯的作品既有力度又有气势,使许多读者对他的形象有了错觉,以为他是个威猛高大的帅哥。可实际上,陈国凯体重不过百,并且自称为“最轻量级运动员”。1987年,湖南出版社邀请一批作家开会,汪曾祺一见陈国凯就哈哈笑道:“你就是陈国凯啊,我以为你长得很高大,原来是这个鬼样子!”陈国凯一下子就被这个可爱的老头逗乐了,也大笑着说:“我原来以为你长得仙风道骨,原来像个酒葫芦!”
(责任编辑:王翔)
声明:文章所有文字、图片和音视频资料,版权均属本网站所有。凡经本网协议授权的媒体、网站,在使用时必须注明“稿件来源:本网站”。
上一篇: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零二】
下一篇:郭进拴|六十岁说【三百零四】